近日,我县80后作者张成的诗集《小村人物》由珠海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由湖北省文联退休编审、原《今古传奇》主编罗维扬整理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刘继明作序,全书萃选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诗歌作品200余首,约5000余行,为作者的首部诗歌作品集。
张成1987年12月出生于竹山宝丰, 13岁时因病辍学,同年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故事等三百余篇(首),六十多万字。2009年10月,其首部中短篇小说集《山的那一头》入围由中央文明办、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等六部委举办的“百位农民作家、百部农民作品”丛书行列,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2010年,其中短篇小说集《绝密行动》由珠海出版社出版发行。2003年以来,作者创作并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作品曾散见于《诗潮》、《绿风》等杂志,《小村人物》为作者的诗歌作品精选集。
8月中旬,罗维扬、张成曾携该诗集样书参加了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诗歌节上,该诗集受到了包括中国诗人北岛、马其顿诗人柳博斯科·扎哈列夫、贝宁诗人霍兰.阿德坎比等国内外著名诗人的好评。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已专门致函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办公室,推荐将该书列入农家书屋采购项目,面向全省农村地区推介。(罗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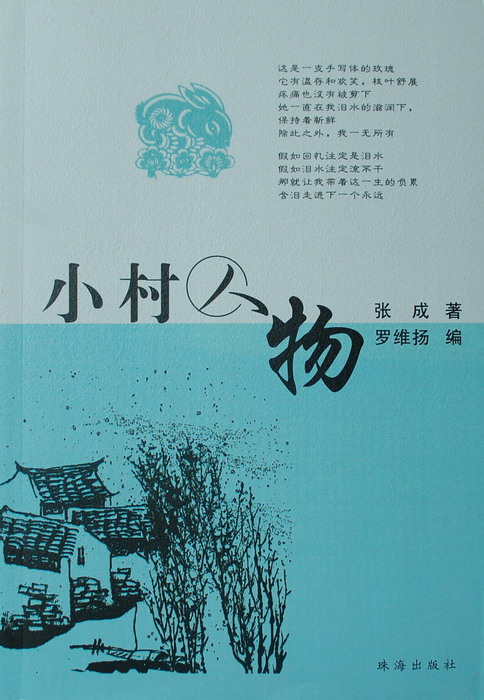
《小村人物》封面
编者的话 ◎罗维扬
2011年3月30日媒体报道:第三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的启动仪式上,主办方抛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来自全国的几十万篇来稿中竟然没有诗歌?难道,当下的青少年已经不写诗不爱诗吗?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曾经作为诗歌最主要受众和拥趸的青少年与诗歌“绝缘”了?
张成似乎是个例外,从十三岁到二十四岁的今年,他一直是爱诗并写诗的。他宣告:“我相信再世俗的生活也有诗”。他能写点旧体诗,这本书却是他最近四年来新诗的选集,长长短短近两百首。
他继承和发扬着“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尤其喜欢读何其芳和舒婷,也读普希金和彭斯。他写各种味道的诗,有土腥气的,有茶叶味儿的,有咖啡味儿的,有奶油味儿的,还有五味杂陈的怪味。味儿是不好形容的,只能尝到了才说“味道好极了!”
张成没有城市户口,只好称他农民;他不会种地,却在深圳、武汉打过几年工,现在仍在家乡打工,做文字工作,也只能叫他农民工。他的诗抒写农民和农村,还对城市、对民族、对世界和宇宙有所感慨,对现实对历史有所观照,更有自身情怀的抒发,爱情的咏叹。
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鲁迅文学奖评委们的注意:在秦巴山脉的旮旯里,有位“八零后”的未名诗人在耕耘,在收获:它不是梨花体,也不是羊羔体,而是张成的诗。
读张成的诗,有的像吸面条,有的像吮橄榄,有的像吃核桃,要砸开外壳,掏取内仁,细嚼慢咽其意象和诗意。
2011年6月21日
张成的诗 (代序)
◎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继明
老作家罗维扬先生向我郑重推荐张成其人其文,并请我为张成的诗集写一篇“序”。我一向觉得“写序”应该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干的活儿,且自认为尚不具备这样的资历,所以过去每逢遇到类似的要求,总是婉言拒绝,可能得罪了一些朋友。这次也不例外。但罗维扬先生第二次提起此事时说:“等你了解张成的经历和作品之后,也许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正是这句话,让我心有所动,并最终把“活儿”接下来了。
我很快收到了罗维扬先生发来的张成诗集电子文档以及他为张成小说集《山的那一头》写的序。在“序”中,罗维扬先生详细介绍了他认识张成的经过,还有他对张成作品的具体分析和评价。认为张成的作品“并不土气,他的先锋性质,不同于一般80后的时髦,或前卫,他也没有所谓的小资情调。张成作品的纯净,凄美,空灵,反映社会生活也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并说,“刘绍棠十三岁发表作品,被称为‘神童’,张成也是十三岁发表作品的,我姑且称他一回天才。”罗维扬先生从发现到不遗余力地扶持和鼓励张成的过程令我感动,但更令人感动的是张成作为一个农村青年,从小身患疑难病症,身处艰苦环境酷爱文学并坚持写作的经历和精神。在浏览张成诗集,读了罗维扬先生随后又发来的张成部分小说之后,我觉得他的评价毫不夸张,也觉得张成是一个天资不凡的青年。“天才,且不幸,就更增加一份沉甸甸的分量了。”
我已很长时间不写诗,也很少读诗了。这些年来,诗坛潮起潮落,论争不断,诗歌观念也在日新月异地变化更新着。但无论艺术形式上怎么变化,诗歌的一些基本品质和传统如“诗言志”和“兴观群怨”等等,恐怕是永远无法“更新”掉的。
读张成的诗,给我最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诗歌和人的内心生活及所处时代的隐密联系。我梳理了一下,张成的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书写个人心迹、感物伤怀的,探问生命意义的如《深入一片蓝》、《白鸟》、《夜鸟》、《玻璃之外》等,其中长诗《堵河之上·蓝色月亮》为难得的佳作,其对于世间万物和生命真谛的问询达到了超出张成年龄的高度和广度,艺术上也情理交融、张弛有度、颇得屈原《天问》之精髓;二是状写乡村人物风俗的,如组诗《小村人物》,这一类作品大都短小精悍,近似于工笔素描,寥寥几笔便能将笔下人物的性格、命运传神地刻画出来,十分生动;三是描写青春和爱情的,如组诗《思念及怀念·致颖》,抒写少年情思,笔触委婉幽微,尤其因作者身染疾患的特殊经验,传达出的情感便更加让人刻骨铭心,其中某些篇什如《命中的月亮》、《到你的声音里取暖》等,即使放在一流的爱情诗中,也堪称佳品;四是针砭时事、讽喻现实的,如组诗《小姐》,将青春和生命遭受的的扭曲植入残酷的现实境遇之中,忧愤和叹惜、抒情与现实汇于一体,具有一种强烈的警世力量。
张成的诗歌(包括小说)将自身特殊体验与人生感悟、现实关怀融会贯通,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人的局限(如某些80后、90后作家热衷的语言游戏、虚拟生活、撒娇和玩世心态),思想视野较为宽广,具备了向上生长和向内掘进的力量。再加上张成对语言的超常敏感和悟性,对各种艺术方法的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使他的写作达到了一种令人注目的境界。
由此,我想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不少身患疾病甚至残疾的人,一旦拿起笔来创作时,他们对艺术和生命的执著探寻和独特表现,往往超出许多“正常人”所能抵达的深度。这一点,中外文学史上不乏经典例证,如卡夫卡、普鲁斯特和史铁生等等,其中的原因实在值得文学评论家们去认真研究。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写过一本《疾病的隐喻》,探讨的就是疾病与艺术和社会人生的秘密联系。
张成的人生阅历和写作成绩,不仅是一个特殊的个案,而且在日益商业化、粗鄙化、功利化和娱乐化的当代背景下,对文学如何从个人和现实出发,捍卫生命的尊严,提升人的品质等等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回答。
 相关新闻
相关新闻




















